公元前475年,孔子刚去世没几年,鲁国人还在为这位“圣人”哭丧,晋国的大街上却没人谈礼仪——老百姓抬头看的,是挂在城墙上的“通缉令”,上面画着范氏、中行氏两家头头的画像;低头聊的,是“智家又占了谁家的地”“赵家的新当家够不够狠”。
这时候的晋国,早不是晋文公重耳当年“退避三舍”称霸的模样了。周天子是个摆设,晋国国君晋出公更惨——连自己的宫殿都快养不起,手里没兵没地,全靠国内六家大夫“接济”。这六家分别是范氏、中行氏、智氏、赵氏、韩氏、魏氏,说好听点是“大夫”,其实就是手握兵权的“土皇帝”,彼此跟街坊抢停车位似的,天天为了地盘打架,打了几十年,终于把范氏和中行氏先打垮了。
剩下的智、赵、韩、魏四家,像四头饿狼盯着一块肉,谁都想多咬一口。其中最凶的那头,是智氏的当家——智瑶,也就是后来人们说的“智伯”。
智伯这个人不是一般的狂,是狂到能把天捅个窟窿的主儿,但你还不能说他没本事——他爹智宣子选继承人时,家里人都反对选智瑶,说“这孩子太傲,迟早把家败了”,可智宣子不听:“我儿瑶文武双全,打胜仗跟喝凉水似的,不选他选谁?”
这话还真没吹。智瑶刚当家没几年,就带着智家的兵把郑国按在地上揍,又把齐国打得不敢出东门,连晋国国君都得看他脸色。有次晋出公想收回点权力,智瑶直接拍桌子:“国君好好待在宫里就行,外面的事我来管。”晋出公吓得差点把茶杯摔了,从此再也不敢提“权力”俩字。
有实力撑腰,智瑶的狂就没了边。他最喜欢干的事,就是拉着韩、魏两家的头头喝酒,喝到一半就开始炫耀:“你们看我智家的地盘,从太行山到黄河边,哪块不是好地?再看看你们韩家、魏家,加起来还没我一半大,以后得听我的。”
韩家的当家韩康子,还有魏家的魏桓子,每次都陪着笑点头,心里却把智瑶骂了八百遍。这俩人都不是软蛋,但没办法——智家的兵力比他们两家加起来还多,真要是翻脸,自家先完蛋。
公元前455年,智瑶觉得“试探”够了,直接派人去韩家要地。要的还不是一般的地,是韩家最肥沃的“万户之邑”——就是能收一万户人家赋税的地盘,相当于现在一个富裕县。
韩康子气得手发抖,刚想拒绝,家臣段规赶紧劝:“主公别冲动。智伯要地不给,他肯定会打咱们;给了他,他肯定还会去要赵家、魏家的地。要是赵家、魏家不给,他们就会打起来,咱们到时候再看情况,总比现在当出头鸟强。”
韩康子想了想,咬着牙把地给了。智瑶拿到地,果然更狂了,没过一个月,又派人去魏家要地,要的也是“万户之邑”。魏桓子的家臣任章也劝:“智伯贪心不足,咱们先顺着他,让他更骄傲,到时候自然有人收拾他。”魏桓子也认怂,把地送了出去。
接连拿到两块肥肉,智瑶更飘了,转头就把主意打到了赵家头上。这次他要的地,是赵家的“蔡、皋狼”——这两块地不是一般的地,是赵家的老根据地,相当于赵家的“祖坟”所在。
赵家的新当家,是赵襄子赵无恤。这人跟韩康子、魏桓子不一样,是个硬茬子。他爹赵简子当年选继承人,出了个怪题:给每个儿子一块竹板,上面写着“治家治国的道理”,说“三年后我要考”。其他儿子都把竹板当宝贝收着,只有赵无恤把竹板上的话刻在脑子里,还专门跑去竹板上写的“常山”考察,回来跟赵简子说:“常山下面有铁矿,能铸兵器;旁边有河道,能引水灌城,这是咱们赵家的宝地。”赵简子一听,当场就定了赵无恤当继承人。
这么个有脑子又硬气的人,怎么可能把“祖坟地”让出去?智瑶派来的人刚说完要地,赵无恤就把桌子一拍:“土地是祖宗传下来的,给不了!”
消息传到智瑶耳朵里,他当场就炸了:“我要地谁敢不给?赵无恤这小子是活腻了!”当天就下令,拉上韩康子、魏桓子,三家联手打赵家。
韩、魏两家心里一百个不愿意,但架不住智瑶的威胁——“你们要是不跟我一起打,我先灭了赵家,再灭你们”,只能硬着头皮出兵。三家凑了十万大军,浩浩荡荡朝着赵家的地盘杀过去。
赵无恤知道自己打不过三家联军,赶紧召集手下商量:“咱们往哪退?”有人说“退到长子城,那城墙厚,能守”,有人说“退到邯郸,那地方粮食多”,赵无恤都摇头,最后说:“退到晋阳。”
晋阳就是现在的山西太原,是赵家经营了几十年的老巢。当年赵简子派家臣尹铎去晋阳当地方官,尹铎问:“主公是想把晋阳当搜刮钱财的地方,还是当保命的根据地?”赵简子说“当然是保命的根据地”,尹铎就去了晋阳,减税减租,还修了水利,老百姓都念赵家的好。而且晋阳的城墙是用“版筑”技术修的,又高又厚;宫里的柱子都是精挑细选的木头,实在不行还能拆下来当兵器;仓库里存的粮食,够吃好几年。
赵无恤带着赵家的兵马和百姓,一路退到晋阳,刚把城门关上,智瑶的大军就到了。接下来的三个月,智瑶天天派人攻城,弓箭跟下雨似的往城上射,可晋阳城墙太硬,守军又拼命,联军连城墙根都没摸到。
智瑶站在城外的高台上,看着晋阳跟块硬骨头似的啃不动,心里也犯嘀咕。他绕着晋阳转了三天,突然看到城外的汾河,眼睛一下子亮了——汾河从晋阳西边流过,水位比城墙还高,要是把汾河的堤坝扒了,水不就能灌进城了?
说干就干,智瑶下令:全军停工,都去挖水渠、扒堤坝。十万人一起动手,没几天就把汾河的水引到了晋阳城下。随着智瑶一声令下,堤坝被扒开,浑浊的河水顺着水渠往晋阳城里灌。
刚开始,水只到脚踝,赵无恤还让人组织百姓往城外排水;可没过几天,水位越来越高,漫到了膝盖,接着又漫到了腰,城里的房子一半都被淹了。老百姓没办法,只能在房梁上搭架子,睡在架子上;粮食吃完了,就杀马吃,马吃完了,就煮木头、剥树皮。
有天早上,赵无恤站在城楼上,看着城里的百姓啃着树皮,心里不是滋味。手下的大臣张孟谈劝他:“主公别担心,老百姓都念赵家的好,就算饿死,也不会投降。”赵无恤点点头,可心里清楚——再这么耗下去,不用智瑶打,城里的人也得饿死。
而城外的智瑶,正得意得不行。他带着韩康子、魏桓子,站在高台上看水灌晋阳,指着城里说:“你们看,我以前还不知道,水这东西能灭一个国家。今天算是见识了——以后谁要是敢不听我的,我就用这招对付他。”
这话一说,韩康子和魏桓子心里同时“咯噔”一下。韩康子悄悄踩了魏桓子一脚,魏桓子也偷偷碰了碰韩康子的胳膊——韩家的都城平阳,旁边有绛河;魏家的都城安邑,旁边有汾河。今天智瑶能用汾水淹晋阳,明天就能用绛河淹平阳、用汾河淹安邑,这话不就是在警告他们吗?
俩人脸上没表现出来,心里却已经开始打鼓:智瑶这人心太黑,就算灭了赵家,下次倒霉的肯定是他们。
而城里的赵无恤,也想到了这一点。他把张孟谈叫到身边,小声说:“韩、魏两家跟智瑶本来就不是一条心,只是怕他才跟着干。你今晚偷偷出城,去见韩康子和魏桓子,跟他们说清楚——赵家灭了,下一个就是他们。”
当天夜里,张孟谈换上老百姓的衣服,趁着天黑,从城墙上吊下来,悄悄摸到韩康子的军营。韩康子听说张孟谈来了,赶紧把他请进帐里,屏退左右。
张孟谈没绕弯子,直接说:“现在智瑶用汾水淹晋阳,看起来是要灭赵家,可赵家灭了之后,他下一步肯定会灭韩、魏。唇亡齿寒,这个道理,大夫您不会不懂吧?”
韩康子叹了口气:“我当然懂,可智伯势力太大,我们要是反了,打不过怎么办?”
张孟谈说:“只要韩、魏、赵三家联手,智瑶的十万大军就是纸老虎。而且智瑶现在得意忘形,根本没防备你们会反——今晚动手,肯定能成。事成之后,赵家愿意把智家的地盘分一半给韩、魏两家。”
韩康子眼睛一亮,又犹豫了一会儿,最后咬着牙说:“好,我跟你们干!”他马上派人去请魏桓子,魏桓子本来就有反心,一听韩康子愿意牵头,当场就答应了。三个人约定:当天夜里,韩、魏两家先派人去扒掉智瑶修的水渠,把水引回智瑶的军营,然后三家一起出兵,杀智瑶一个措手不及。
当天半夜,晋阳城外突然乱了起来。韩、魏两家的士兵偷偷摸到水渠边,把堤坝扒了个大口子,原本灌向晋阳的河水,一下子掉头冲向智瑶的军营。智瑶的士兵大多在睡觉,听到水声以为是山洪,慌得连衣服都没穿就往外跑,军营里到处都是哭声和喊声。
就在这时,赵无恤亲自带着晋阳的守军杀了出来,韩康子、魏桓子也带着自家的兵冲了上去。三家兵马像三把刀子,扎进智瑶的军营里。智瑶从梦里被吵醒,刚想披甲上阵,就被赵无恤的手下抓住了。
第二天早上,战斗结束了。智瑶的十万大军死的死、降的降,智家的族人也被抓了个干净。赵无恤看着被绑在面前的智瑶,想起这几个月晋阳被淹的惨状,气得一刀砍了他的头,还让人把他的头骨做成了酒器——每次请客吃饭,都要用这个酒器喝酒,算是报了仇。
智瑶一死,智家彻底完了。赵、韩、魏三家把智家的地盘分了个干净,每家的地盘都比以前大了一倍。这时候的晋国国君晋出公,看着三家越来越强,心里害怕,想偷偷联合齐国、鲁国来打三家,结果消息走漏,被三家赶下台,最后死在了逃亡的路上。
晋出公死后,三家立了个新国君,可这个新国君比晋出公还惨,连祭祀祖宗的钱都得跟三家要,完全是个傀儡。公元前403年,赵、韩、魏三家觉得“傀儡国君没意思”,干脆派使者去见周天子,要求周天子封他们为“诸侯”。
周天子这时候早就没了实权,不敢得罪三家,只能点头答应,正式封赵烈侯(赵无恤的后代)、韩景侯(韩康子的后代)、魏文侯(魏桓子的后代)为诸侯。从这时候起,晋国就分成了赵国、韩国、魏国三个国家,历史上把这件事叫做“三家分晋”。
三家分晋这事儿,看着是三个大夫抢了一个国家的地盘,其实是历史的一个大转折——在此之前,还是“春秋时期”,虽然周天子没权力,但各国还讲究“礼仪”,打仗也有规矩;可三家分晋之后,“战国时期”就来了,各国之间再也不讲规矩,只要能抢地盘、灭国家,什么招都能用,比如后来秦国灭六国,就是靠“狠”和“诈”。
而且,三家分晋让其他国家学乖了,齐国的田氏看着赵、韩、魏能分晋,也学着把齐国的国君赶下台,自己当了诸侯;鲁国、郑国这些小国,也慢慢被大国吞并。整个天下,从原来的“几十个国家”,慢慢变成了“战国七雄”——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秦,这七个大国,开始了长达两百多年的混战。
很多年后,有人问魏文侯:“当年你爷爷魏桓子跟着赵无恤反智瑶,就不怕失败吗?”魏文侯笑着说:“怕肯定怕,但更怕的是被智瑶灭了。有时候,拼一把还有活路,不拼就只能等死。”
这话其实说透了三家分晋的道理——智瑶不是输在实力上,是输在“太狂”,把能团结的人都逼成了敌人;而赵、韩、魏三家,不是赢在运气上,是赢在“懂变通”,知道什么时候该忍,什么时候该拼。
历史就是这样,有时候一个人的狂妄,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;有时候几个小人物的联手,能翻开历史的新一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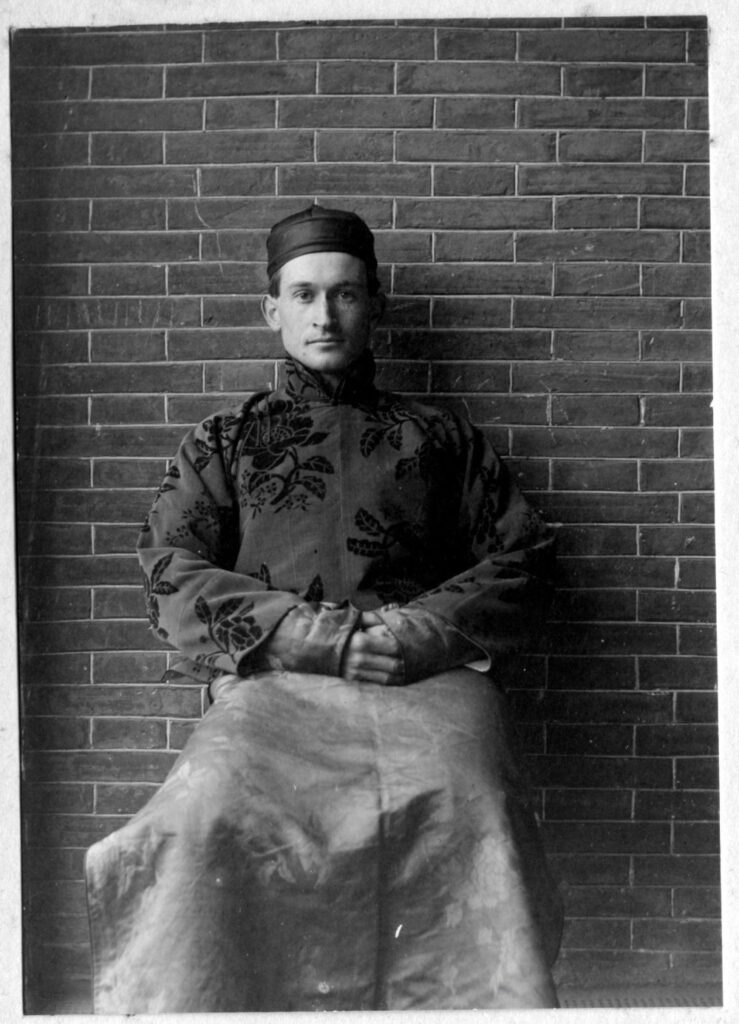

三家分晋:春秋的句号,战国的开场哨:等您坐沙发呢!